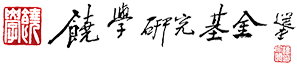季羨林談饒宗頤
季羨林談饒宗頤
2014-10-08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饒宗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台灣、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國家,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
幾年以前,饒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選堂集林‧史林》三巨冊寄給了我。我仔細閱讀了其中的文章,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大陸的同行中,我也許是讀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比較多的。因此,由我來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和學術造詣,可能是比較恰當的。中國有一句古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紹,饒先生的學術成果,一旦在大陸刊佈,自然會得到知音。但是,介紹一下難道不會比不介紹更好一點嗎?在這樣的考慮下,我不避佛頭著糞之譏,就毅然答應寫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幼承家學,自學成家。自十八歲起,即嶄露頭角。此後他在將近五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在學術探討的許多領域裡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至今不衰。饒宗頤教授的學術研究涉及範圍很廣,真可以說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要想對這樣浩瀚的著作排比歸納,提要鉤玄,加以評價,確非易事,實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是必須隨時應用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只有這樣,學術研究這一條長河才能流動不息,永遠奔流向前。討論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我就想從這個觀點出發。我想從清末開始的近一百多年來的學術思潮談起。先引一段梁啟超的話:
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識略》,穆有《蒙古游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畬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誌》,開始端緒,而其後竟不光大。近人丁謙於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餘種,頗精贍。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接著又談到金石學、校勘、輯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學是清代後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學術史上,這是一個新動向,值得特別重視。金石學等學問,雖然古已有之,但此時更為繁榮,也可以說是屬於新興學科的範疇。這時候之所以有這樣多的新興學科崛起,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趙甌北的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應用到學術研究上,也是適當的。世界各國的學術,都不能一成不變。清代後期,地不愛寶,新材料屢屢出現。學人的視野逐漸擴大。再加上政治經濟的需要,大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新興學科於是就蓬蓬勃勃地繁榮起來。
下面再引一段王國維的話: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經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蹟,至今遂成為中國史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錄一:《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王國維講,方壯猷記註)
這裡講的就是我在上面說的那個意思。王國維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我覺得,王靜安先生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是實事求是的,是正確的。
近百年以來,在中國學術上,是一個空前的大轉變時期,一個空前的大繁榮時期。處在這個偉大歷史時期的學者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意識到這種情況,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投身於其中。有的學者仍然像過去一樣對新時代的特點視而不見,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結果是建樹甚微。而有的學者則能利用新資料,探討新問題,結果是創獲甚多。陳寅恪先生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一九八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詞“預流”,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形象的名詞。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可以說,王靜安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援庵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預流果的,近代許多中國學者都得到了預流果。從饒宗頤先生的全部學術論著來看,我可以肯定地說,他也已得到預流果。
我認為,評價饒宗頤教授的學術成就,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談到對饒先生學術成就的具體闡述和細緻分析,我想再藉用陳寅恪先生對王靜安先生學術評價的幾句話。陳先生說: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生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與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陳先生列舉的三目,我看,都可以應用到饒先生身上。我在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一、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
饒宗頤教授在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顯著的。一方面,他對中國的紙上遺文非常熟悉,了解得既深且廣。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視國內的考古發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遊,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地下發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對國外的考古發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國內一些偏遠地區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而饒先生則無不注意。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饒先生利用碑銘的範圍很廣,創獲是非常突出的。從中國藏碑一直遠至法國所藏唐宋墓誌,都在他的視野之內。《論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一文主要從中國書法的觀點上來研究伯希和攜走的三個唐代拓本。在《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他利用碑銘探討了武后的信佛問題。幾十年以前,陳寅恪先生在他的論文《武曌與佛教》中曾詳細探討過這個問題。他談的主要是武后母氏家世之信仰和她的政治特殊地位之需要。他指出,武后受其母楊氏之影響而信佛,她以佛教為符讖;他又指出,《大雲經》並非偽造;對唐初佛教地位之升降,他作了詳細的分析。總之,陳先生引證舊史與近出佚籍,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陳先生學風謹嚴,為世所重;每一立論,必反覆推斷,務使細密周詳,這是我們都熟悉的。但在《武曌與佛教》這一篇文章中,陳先生沒有利用石刻碑銘。饒先生的這一篇文章想補陳先生之不足,他在這裡充分利用了石刻。他除了證實了陳先生的一些看法之外,又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指出,武后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度有大轉變,晚年她由佛入道;他又指出,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之行動,乃承繼高宗之遺軌。陳、饒兩先生的文章,各極其妙,相得益彰,使我們對武后這一位“中國歷史上最奇特之人物”(陳寅恪先生語)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
二、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
饒宗頤教授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一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中外關係的研究基本上也屬於這一類。在饒先生的著作中,中外關係的論文佔相當大的比重,其中尤以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更為突出。我就先談一談中印文化交流的問題。
在《安荼論與吳晉間之宇宙觀》一文中,饒先生從三國晉初學者,特別是吳地學者的“天如雞子”之說,聯想到印度古代婆羅門典籍中之金胎說,並推想二者之間必然有某種聯繫。中國古代之宇宙論,僅言鴻濛混沌之狀,尚未有以某種物像比擬之者。有之,自三國始。漢末吳晉之渾天說以雞卵比擬宇宙。印度佛經中講到許多外道,其中之一為安荼論,他們就主張宇宙好像是雞子的學說。印度古代許多典籍,比如說梵書、奧義書、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等等,都有神卵的說法。估計這種說法傳入中國,影響了當時中國的天文學說,從而形成了渾天說。最初宣揚這種學說的多為吳人。這種情況頗值得深思,而且也不難理解。吳地瀕海,接受外來思想比較方便。陳寅恪先生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講的就是這種情況。
大家都知道,中印文化交流關係頭緒萬端。過去中外學者對此已有很多論述。但是,現在看來,還遠遠未能周詳,還有很多空白點有待於填充。特別是在三國至南北朝時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頻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廣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在科技交流方面,我們的研究更顯得薄弱,好多問題我們基本沒有涉及。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多得很,我們絲毫也沒有理由對目前的成績感到滿意,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我們要向饒宗頤教授學習,在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上,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果。
除了中印文化關係以外,饒先生還論述到中國在歷史上同許多亞洲國家的關係。《早期中日書法之交流》這一篇論文,講的是中日在書法方面的交流關係。 《說詔》一文講的是中緬文化關係,《阮荷亭往津日記鈔本跋》則講的是中越文化關係。這些論文,同那些探討中印文化關係的論文一樣,都能啟發人們的思想,開拓人們的眼界。我在這裡不再細談。
三、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
我在這裡講的外來觀念是指比較文學,固有材料是指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饒宗頤教授應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的源流,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有很多啟發。
在《〈天問〉文體的源流》一文中,饒先生使用了一個新詞“發問文學”,表示一個新的概念。他指出,在中國,從戰國以來,隨著天文學的發展,“天”的觀念有了很大的轉變。有些學者對於宇宙現象的形成懷有疑問。屈原的《天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出來的。饒先生又進一步指出,在《天問》以後,“發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個支流,歷代幾乎都有摹擬《天問》的文學作品。饒先生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上探討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種“發問文學”是源遠流長的。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經典中都可以找到這種文學作品。他引用印度最古經典《梨俱吠陀》中的一些詩歌,以證實他的看法。他還從古伊朗的Avtsta和《舊約》中引用了一些類似的詩歌,來達到同樣的目的。中國的《天問》同這些域外的古經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蘇雪林認為可能有淵源的關係,並引證了印度的《梨俱吠陀》和《舊約》。饒先生似乎是同意這種看法。我自己認為,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就下結論,似乎是為時尚早。但是,不管怎樣,饒先生在這一方面的探討,是有意義的,有啟發的,值得我們認真注意。
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緻,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給我們以啟發。我決不敢說,我的介紹全面而且準確,我只不過是盡上了我的綿薄,提出了一些看法,供讀者參考而已。
如果歸納起來說一說的話,我們從饒宗頤教授的學術論著中究竟得到些什麼啟發、學習些甚麼東西呢?我在本文的第一部份首先提出來一個重要的問題: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必須隨時接受新東西。我還引用了陳寅恪先生的“預流果”這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我在這裡再強調一遍:對任何時代任何人來說,“預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做甚麼事情,都要預流,換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跟上時代的步伐生產、建設,無不有跟上時代的問題。學術研究何能例外?不預流,就會落伍,就會僵化,就會停滯,就會倒退。能預流,就能前進,就能創新,就能生動活潑,就能逸興遄飛。饒宗頤先生是能預流的,我們首先應該學習他這一點。
預流之後,還有一個掌握材料、運用材料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進行學術研究,掌握材料,越多越好。材料越多,在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方法的指導下,從中抽繹出來的結論便越可靠,越接近真理。材料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們往往囿於舊習,片面強調書本材料,文獻材料。這樣從材料中抽繹出來的結論,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性與狹隘性。我們應該像韓愈《進學解》中所說的那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畜,待用無遺。”我在上面已經多次指出,饒先生掌握材料和運用材料,方面很廣,種類很多。一些人們容易忽略的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都被派上了用場,有時甚至能給人以化腐朽為神奇之感。這一點,我認為,也是我們應該向饒先生學習的。
中國從前有一句老話:“學海無涯苦作舟。”如果古時候就是這樣的話,到了今天,我們更會感到,學海確實是無涯的。從時間上來看,人類歷史越來越長,積累的歷史資料越來越多。從空間上來看,世界上國與國越來越接近,需要我們學習、研究、探討、解釋的問題越來越多。專就文、史、考古等學科來看,現在真正是地不愛寶,新發現日新月異,新領域層出不窮。今天這裡發現新壁畫,明天那裡發現新洞窟。大片的古墓群,許多地方都有發現。我們研究工作者應接不暇,學術的長河奔流不息。再加上新的科技成果也風起雲湧。如今電子計算機已經不僅僅限於科技領域,而是已經闖入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藩籬。我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再也不能因循守舊,只抓住舊典籍、舊材料不放。我們必須掃除積習,開闊視野,隨時掌握新材料,隨時吸收新觀點,放眼世界,胸懷全球;前進,前進,再前進;創新,創新,再創新……願與海內外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
時為農曆中秋,誦東坡“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之句,不禁神馳南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