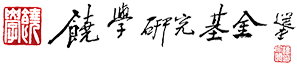Daoist Studies by Prof. Jao Tsun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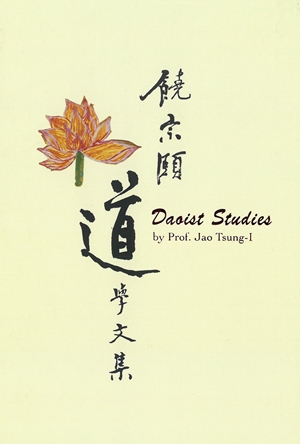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序〉
恩師饒宗頤教授是當今國學泰斗,同時也是當今世界上少數的道學(道家和道教之學)專家權威之一,要為他的《道學文集》寫序文是十分榮幸之事,我自然樂意為之,可是,我何德何能竟被編輯選中和委以此「重任」?故此,與其說寫序文,倒不如說讓我略為談談我對饒師在道學研究方面的個人感受或親身體驗比較妥當一點,適合一點。
我追隨饒師讀書始於一九六四年,當時饒師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而我從饒師研究道教則始於一九六七年,當時我從饒師攻讀碩士學位,專門研究金元詞。由於金元時代道教流行,尤其是全真教正如日中天,極為興盛,而全真教的多位宗師都寫下大量的詞作,所以他們的詞集皆在我研究範圍之內;亦因此,我對道教,甚至道家的各方面知識,都要去正面接觸和認識,這就使我進入道學研究的領域。
當時我對全真詞認識實在很淺,幸而我掌握到饒師的《詞籍考》一書(一九六三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它十餘篇詞集考的精簡文章裏我得到了我需要的材料和專門知識,認識到全真詞的特色和每位全真教宗師的不同詞風,這給我極大的幫助,為我解決了不少疑難。我真如在黑夜大海茫茫之中看到了明燈﹗饒師的考據文章給我無限的安慰和鼓舞,同時也為我提供了不少研究全真詞的推動力。後來我對全真詞念念不忘,寫了好幾篇有關全真詞(或說為全真教多位宗師的詞)的文章,全賴《詞籍考》一書對我的啟發﹗
有一點,於此不能不提的是,經饒師的考證,詞調《鶯啼序》(二百四十字)並不如一般詞學家所說,始於吳文英(一二一二?至一二七六?),實際上遠在吳氏之前的全真教祖師王重陽(一一一二年一一七零)已填此調了﹗此調見王氏《重陽全真集》卷四。
以上種種,都是饒師在詞學方面的新發現,也當然是對道學的巨大貢獻。饒師為我們在詞學和道學方面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或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怎能不敬佩他的異於常人的研究成果和超人的學識呢?
又,在那個時期,為了追蹤全真教的來龍去脈和其他相關的問題,我開始認真地讀一些道籍。第一本要讀的自然是老子的《道德經》。但《道德經》的注本不少,如《河上公章句》、《王弼注》等等都要讀的,至少是要參考的。但它們是否能夠釐清道教與《道德經》的密切關係呢?饒師提議我讀——小心去讀《老子想爾注》。這樣,我就聽從饒師的吩咐小心翼翼地讀他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老子想爾注校箋》(全名為《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誰知不讀則已,一讀則獲益大了﹗道教——尤其是初期道教與《道德經》的千絲萬縷的關係都能於此書裏得到釐清,顯示無遺。這完全是拜饒師的詳盡校箋所賜。因此,《老子想爾注校箋》便被認為是道教研究入門的必讀書,廣被世界各國道教研究學者推崇。當今歐洲著名漢學家施舟人教授 (K. M. Schipper,一九三四年出生) 於其〈饒宗頤先生的《老子想爾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學的發展〉一文這樣稱讚饒師:
饒宗頤先生是道教研究的開拓者。他不僅把蒙塵已久的重要文獻搶救出來,並加以各種嚴謹的注釋與考證。可以說,在他之前,從未有人如此科學地研究道教文獻。……《老子想爾注校箋》……提供了一個暸解漢代思想的全新角度。
施舟人教授之言十分中肯,毫不誇張。有《老子想爾注校箋》的研究成果作為研究道教的底子,我信心十足地研究全真教的歷史和全真教的文學作品。
在撰寫碩士論文《金元詞通論》之際,我為自己定下一個計劃:待我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我一定跟饒師全面深入地研究全真教文學——尤其是詞,作為我攻讀博士學位的題目。可是,正當我的研究工作剛剛做畢和即將動筆撰寫論文的時候,饒師便離開港大跑到新加坡大學去當系主任和創系教授了﹗無可奈何,我唯有轉到羅慷烈教授門下,勉強完成我的碩士論文。本來,我早就打算追隨饒師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和研究全真教文學的,不幸此際饒師已然遠去新大,而羅師又不是道教專家,我只好暫時放棄繼續讀書的念頭,申請入港大亞洲研究中心作研究助理,負責蒐集二三十年代的粵劇劇本、編劇目和嶺南畫派的研究。不過,對道教的興趣並無稍減,我耐心地等待機會。幸得羅教授的提議和推薦,我終於成功進入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追隨另一位道教權威柳存仁教授研究道教,時為一九七二年十月。但幾經探索、考慮和與柳師商議,我從原來希望研究全真教文學轉變為研究道教宗派史,尤其是明清時期的道教宗派史,最後集中精力專注武當派的歷史,結果花了差不多四年時間完成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為 “On the Cult of Chang San-feng and the Anthenticity of his works”(《張三丰信仰及其著作真偽研究》),是用英文寫的。
一九八一年我辭去西澳洲Murduch大學的教職,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雖然我主要教文學——詞和曲,但同時亦教「道教史」(是「宗教史」的一個環節),所以我仍然關心學界道教研究的成果,而饒師的文章我一篇也沒有忽略。它們不獨為我提供新的專門知識,更給我無限鼓舞,時時提醒我要「見賢思齊」,催促我繼續研究道教﹗
此次為了寫這篇序文,我重讀多篇以前讀過的饒師文章,更遍讀文集裏的六十六篇文章,「溫故知新」,我獲益實在匪淺﹗獨是這幾十篇「短文」已可窺見饒師在道教研究上的驚人成績了﹗
這六十多篇文章,此集的編輯把他們分作六類:道教探原、道學、道教文學藝術論、序跋、道教經籍目錄、道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另外有兩篇附錄。它們涵蓋的範圍實在很廣,有老學、莊學、人物(包括仙家)、道經、醫學、養生學、文學(尤其是詩詞)、藝術、民間信仰、善書、三教關係、楚文化、戲曲、小說、煉丹學、哲學等多門學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饒師在道學方面廣博的知識。不過,「廣博」並不能充分標誌饒師在道學的成就,也不能充分指出饒師在其他學問的成就。廣博或淵博,只是其中一點而已。雖然如此,廣博或淵博,無疑是饒師學問的一個很大很不尋常的特色,可以說,當今的學者,或甚至近百年來的學者,無人能及﹗實際上,饒師在敦煌學、甲骨學、簡帛學、詞學、史學(包括潮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金石學、文學、琴學、宗教史、梵學、中外關係史、藝術史、翻譯等等十多門學問都有超人的成就,為國學研究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饒師的道學研究只不過是宗教史其中一個小環節而已。環節雖小,但牽涉的範圍卻是廣大的。以小見大,在道學範圍已經可以見出來了。世人愛將饒師與季羨林教授(一九一一至二零零九)或錢鍾書教授(一九一零至一九九八)相比,譽為「南饒北季」或「南饒北錢」。我認為,若從學問淵博的角度去看,季羨林教授和錢鍾書教授是比不上饒師的。倘若加上在藝術(繪畫與書法)造詣上的成就,季、錢兩位教授就是更無法與饒師相比了﹗又有外國學者愛將饒師與王國維先生(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七)相提並論,認為王先生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國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而後半期則是饒師;王先生的學問以精取勝,而饒師則以博取勝。這一說法,我頗為同意。但要專精並不太難,要達到廣博就很不容易了,因為要學問廣博,需要關注的範圍大、層面多、點數眾,要花很大精力和時間,並不是一般學者可以做到的。我頗認為,由博而精較易,由精而博就很難了。學問博的學者可稱為通人,而學問精的學者只是某門學問的專家而已,其中的分別是很大的。我羨慕通人,因為我知得太少,極其量只可以說是一兩個小範圍的專門知識比一般學者多一點而已,真是很無奈的。
如果我們認同饒師學問的特色是廣博或淵博的話,饒師的研究課題的特色便是新奇——新穎奇特。就是說,他的研究課題是前人未有研究過,或只有提出過而未作深入或全面研究過的。就本《文集》我便可以舉出幾篇作為例子,如〈(傳老子師)容成遺說鉤沉——先老學初探〉、〈劍珌行氣銘與漢簡《引書》——附瑜伽安心法〉、〈中黃子孝〉、〈《太平經》與《說文解字》〉、〈關聖與鹽〉、〈關於《青天歌》作者〉、《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植》、〈《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南戲戲神咒(囉哩嗹)之謎〉等等都是頗為新奇的課題,裏面談到的皆為前人所未注意到或未論及的學術專題。季羨林教授曾經說過,饒師「最能發現問題,最能提出問題」,可謂獨具慧眼!但是「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不是憑空可以做到的,它們俱植根於博學。學不博便不能發現問題,亦無從提出問題。問題的發現與提出是從博學「提煉」出來的。博學是根是本,問題是花是果。饒師的學問博大淵深,瓣瓣精通,左右逢源,他自然比一般學者易於「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了,而且他發現和提出的問題往往都是很新奇的。這實際上是創新——學術上的創新,如同饒師在藝術上的創新一般。
饒師在學術上的創新實在很常見的。他在十多門學術研究裏,每一門都有創新之作,如上文提到的《老子想爾注校箋》,為世上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的第一本著作;又如〈《太平經》與《說文解字》〉是第一篇研究《太平經》與《說文解字》關係的文章;又如〈《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是第一篇利用《太清金液神丹經》討論南海地理的文字。最使我佩服的是,饒師竟花了十年時間將以巴比倫古楔形文字寫成的蘇美爾人開天闢地的神話翻譯成中文,是為巴比倫史詩的第一部大譯本,名為《近東開闢史詩》,面世於一九九一年。這無疑是翻譯學上的創新,在翻譯史上應佔一特殊位置。饒師之所以有如此高強的翻譯能力全賴他能通七國語言。這自然是學問的「博」的一個明證。故此,做學問,我認為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博學」。先博學,然後才可以談論其他。
饒師博學是世界公認的,毋容置疑,但他為甚麼能「博」呢?最重要的是他讀書多,古今中外的書他都讀,只要他有能力——語言能力去讀他便讀。首先是他的國學底子非常好,自小便得到嚴格的訓練。同時,他愛讀書,經、史、子、集無一不讀,而且熟讀。故此,他能打通文、史、哲、藝,左右上下,到處逢源,觸類旁通。這就是他能夠在十多門學問中都有出色表現的首要原因。無論他寫一篇文章或一本書,他運用的材料不限於某一門學問,而是多利用其他部門的材料,所謂「旁徵博引」,這樣,他的普作不獨材料豐富、層面多、說服力強,而且立論精確。我又再舉《老子想爾注校箋》為例,表面上,它不外是道經的研究,但實際上它跨越了多個學術研究範疇。它是考據學、版本學、目錄學、道教史、經籍學、史學、敦煌學、思想史、文字學等等的結晶品,就是說,它是多門學問「提煉」出來的成果。沒有廣博的學問,沒有多門學問的專業知識是產生不了如此的驚世鉅著的。這種跨越多個學術部門的專業知識的現象,當我們閱讀這本《文集》裏每一篇的時候都會清楚地見到或至少感悟得到,於此毋庸詳述。
說到研究和撰述,饒師的態度是十分嚴謹精密的。雖然蒐集研究材料時「寧濫勿缺」,但真正運用之時,饒師非常小心,只用其可信的,精要的。他不單止運用文獻上的材料,還適當地運用田野考察所得的材料,甚至甲骨文的材料、簡帛學的材料。總之,材料的來源儘量多元化,絕不靠孤證。這是「多重證據法」。我覺得考據學是饒師的強項,這當然是受了清儒主張「證據周遍」的考據學影響所致。原來饒師於清代學者之中,最佩服的是顧炎武(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和孫詒讓(一八四八至一九零八)。顧氏治學嚴謹,對問題愛窮研究底;而孫氏精於甲骨之學,為甲骨學開山之祖。而今饒師對學術上的疑難問題窮追不捨和對甲骨學的終身研究無疑是受了這兩位樸學大師的影響。
對於研究課題,饒師主張「小題大做」。即是說,題目雖小,但要研究得周全、深入、透徹,目的是要儘量不留給他人再作研究的餘地,而得出來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終極結論。換言之,就是得其「盡」。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饒師的著作不獨嚴謹,而且非常精密,絕少人能夠找出瑕疵去反駁和提出不同的結論的。
故無論是道學的研究,或其他學術範疇的研究,饒師之所以有驚人的成就和巨大的貢獻,首先是他博學,然後從博學裏「提煉」出問題——新奇的問題,繼而以嚴謹的態度去研究它們,最後以精密的方法寫成論著。試問,基於以上種種,產生出來的成果,寫出來的文章、專著,哪有不精之理呢?哪有不令人震驚、佩服之理呢?可是,一般的學者連第一個層次的資格都沒有,又怎會有第二、第三個職次?亦當然寫不出像樣的東西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道學研究是日本人、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的天下,但五十年代之後,便不是他們外國人的專利了,原因是我們出了如饒師等兩三位國際著名的大學者,道學專家、大師。憑着他們在道學研究上的努力、撰述和貢獻,憑着他們帶領一批弟子從事研究道學,道學的園地,至少一半已從外國人的手中爭奪回來,再不讓外國人專美了!而今,外國人對饒師讚頌不已,稱他為「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施舟人教授語),而國人稱他為「中國的驕傲」(當代語言學家許嘉璐教授語),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與饒師在道學方面的成就有絕對關係。
毫無疑問,饒師是道學大師,不,應該是大師大的大師!
以上東拉西扯,寫成了這篇不像序文的序文,頗感慚愧!本人才疏學淺,只好如此應編輯之命而已。希望讀者原諒和接受這樣的一篇序文;更深盼饒師看了這篇不像樣的序文後不致怪我「不學無術」便很滿足了。但願如此!
黃兆漢 於澳洲塔省倚晴樓晴窗下,時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